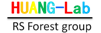普朗克在物理学领域是如雷贯耳,因为发现普朗克常数,催生了量子物理的出现,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马普协会也是为纪念马克斯·普朗克而改名的。在遥感领域,也因为提出黑体辐射和普朗克函数成为热红外遥感的基石。但是在教材中,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组定义和公式,包括黑体定义、维恩公式、瑞利-金斯公式到普朗克函数等,但背后其实蕴含着很多故事,发人深省。
首先,普朗克函数的提出里面有一个人的贡献很重要。那就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海因里希·鲁本斯。普朗克说过“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Ruben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radiation law and thereby the foundation of quantum theory would perhaps have arisen in quite a different manner, or perhaps not have developed in Germany at all.” (没有鲁本斯的介入,黑体辐射定律的建立和量子理论提出的进程就会完全不同,很可能根本不在德国发生和发展。)为什么呢?实际上,普朗克一直是维恩定律的支持者。1896年后,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进一步从统计物理和电磁场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和论证维恩的公式,以为这就是黑体辐射的普遍规律。但是,就在1900年10月7日,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鲁本斯夫妇应邀到普朗克家小憩,相叙甚欢。告别之前,鲁本斯告诉普朗克一事,不禁令普朗克大吃一惊。鲁本斯提到,1900年6月瑞利(Rayleigh)发表了一篇犀利的短文,对维恩公式的普适性提出异议,当温度和波长均高时,或它们的乘积λT够大时,误差会显著增大。鲁本斯随意提及的这件事情,本意是因为论文中瑞利引用了他的远红外波段的一些工作,比较得意。但是,普朗克却很受刺激,毕竟这挑战了他维护维恩公式的信念;他都投入了6年多的心血呀。鲁本斯唤醒了普朗克,使普朗克对当时黑体辐射问题的形势,尤其是瑞利的挑战,有了全新的正确的认识。鲁本斯夫妇前脚刚刚离去,普朗克后脚就急急忙忙把自己关进了书房。摆脱了论证维恩定律的局限,很快解决了问题,成为普适的黑体辐射定律的开创者与发现者。但是,他的第一个有关报告仍冠以“维恩能谱公式之改进”的标题。
第二个有意思的事情是普朗克的纠结。普朗克早期颜值很高,温文尔雅、气质不凡。在学习物理之前,普朗克会钢琴、管风琴和大提琴等,险些选择音乐专业。但普朗克最后还是选择了学习物理,并将自己的决定解释为 “生命中最崇高的科学追求”。慕尼黑的物理学教授菲利普・冯・约利曾劝说普朗克不要学习物理,他认为 “这门科学中的一切都已经被研究了,只有一些不重要的空白需要被填补。” 这也是当时许多物理学家所认为的。但是,普朗克没有纠结很久,就回绝了好意,认为:“我并不期望发现新大陆,只希望理解已经存在的物理学基础,或许能将其加深。”真正的纠结是他发现了量子和普朗克函数,是否要坚持这个发现和解释。当时条件下,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令人鼓舞的新事物,但是不太符合常识和认知,也存在着很多流言蜚语。有的说,在维恩和瑞利之间做出“插值”不过是玩弄一些计算方法;有的说对量子基元的存在不能理解,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违反经典统计物理中的能量均分定理。这也导致普朗克非常小心,反映了经典物理学的束缚,反映了他的内心挣扎和纠结。有很多文章,在充分肯定普朗克的渊博精深的同时,又把普朗克称为内心不情愿的革新者 (reluctant revolutionary)。可能是因为这些纠结,他的颜值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兴趣的可以查查。
当然,普朗克函数的发现肯定不是简单的“插值”。只有物理学功底极其深厚才有可能做到。毕竟,无论是电磁场理论、热力学,还是统计物理,都属于19世纪下半叶刚成雏形的新兴物理分支,而当时能同时懂得热力学、统计物理和电磁场的人很少,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者,非普朗克莫属。
其实,瑞利、维恩和普朗克先后在1904年、1911年和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普朗克量子论提出后的5年他的工作几乎无人问津,直到1905年爱因斯坦发展了量子论,提出光量子概念并成功解释光电效应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普朗克量子论的巨大价值。因此,在量子发现和被接收的过程中,普朗克也感悟很多。他在自传中写道:“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靠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而主要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了,熟悉这一真理的新的一代成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