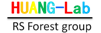陈镜明老师是我非常佩服的牛人之一。他的光环和头衔很多,多伦多大学地理与规划系教授、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2010)、加拿大高级首席科学家(2003)、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2006),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主编等等。但是我更关注的是他的成长历程。18年的一次聚会中,陈老师非常谦逊,告诉我说他的大多数成果,包括LAI2000,BEPS模型,都是在我这个年龄段做出来的,让我备受鼓舞。我试图去了解他的学术经历,以期获得一些启示。
目前,在学术上,陈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情:
(1)大胆提出LAI的定义问题:植被叶片的疏密程度常用叶面积指数(Leaf Area Index, LAI)来表征。用叶面积指数来刻画叶片的疏密特性最早出现在作物学领域,它被定义为单位地表面积上单面植物光合作用面积的总和。生态学家们已经广泛接受这个定义。但是这一定义难以适用于非扁平叶面的植被,比如针叶或者卷曲的阔叶。怎么办?也曾有人提出用投影面积,但不够普适。1992年,陈老师和Black提出将叶面积指数定义为单位地表面积上绿叶表面积总和的一半,兼容了针叶和阔叶。这种创新还是非常需要勇气的,那时候陈老师36岁。
(2)聚焦方向不断引领创新的能力:陈老师一直围绕的都是碳循环。碳循环中叶片是关键问题。先解决叶面积的问题,比如LAI要首先定义好,然后怎么测量呢?于是发明叶面积指数观测仪器。直射光环境怎么测量?散射光环境如何测量?从这些问题分别搞出来LAI 2000和鱼眼照相技术等。传统大叶模型有问题,那么就要区分光照和阴影叶片建模。NPP和GPP怎么模拟和预测呢,于是研发了BEPS和InTEC模型。这些模型后来也在中国的多个区域得到实证,成功计算了全中国1 km分辨率1900-2000 年的森林碳源汇分布并预测了未来100 年的趋势,被中国国家发改委列为一个重要的参考结果。那么,光合作用还和什么有关系?羧化速率、叶绿素等等。于是逐个进行攻克。目前已近70岁,还在制作全球的叶绿素分布图。陈老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继续碳循环研究,带动一个方向的发展,培养一大批人。